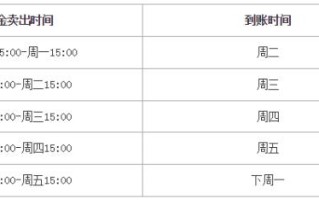本故事已由作者:梅三娘,授权每天读点故事app独家发布,旗下关联账号“每天读点故事”获得合法转授权发布,侵权必究。
凤兰站在门口怔怔地看着街上的人慌张逃窜,来不及细打听,赶紧将大门锁好,又加了一道门闩,几乎是连滚带爬赶来禀报:“大娘子,大街上全乱了!”
“出了什么事情?”
凤兰着急地摇摇头,瞪大了眼睛告诉我,一定是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情。这还是她头一次见街上的商贩连物品都不收拾,就赶紧往家里跑。
吩咐了人偷偷从后院跑出去打听,好半晌才见人慌张进了屋子禀报:
“说是有几个契丹人在市井为非作歹,衙门派去的三个官兵还没来得及拔刀,就被杀了。领头的是一个健壮的家伙,逢人就要拉过来恐吓几句,见着漂亮姑娘还要搂进怀里调戏一番。大娘子,要是他们闯进府里,这可如何是好?”
凤兰皱着眉也在一旁喋喋不休:“偏偏是这个时候,咱们侯爷不在家。府中上下都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孺丫头,再好的,也只有七八个会些拳脚功夫的老伙计,能不能打得过尚且两说呢。”
“先别着急。”
说这话时,我的心里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害怕。侯府这么大一个门面,若这伙人是为了敛财,定然不会放过咱们。
我极力安慰自己冷静,像是对他们说,又像是自言自语:“汴京是官家住的地方,出现官兵横尸街头,已然算是大事。既已是大事情,此刻一定已经有人去宫中禀报。官家不会纵容这帮外来的人辱没了天威,再等等,会有办法的。”
1
这样等了好一会儿,趴在门缝里往外面看,街上已经空无一人,侧着耳朵听,也没见什么大的声响,心里的石头总算是放下些。
“开门!开门!”
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吓得府中众人捂嘴震惊,胆子小些的女使,已经红了眼眶,全身战栗着缩在墙角。
这会子,下人们齐刷刷将目光看向了我,眼见着此景,总要有人站出来拿个笃定的主意才是。
“守……守着门,拿梯子站到墙根上去看看,外面都是些什么人。”我能明确感觉到自己声音的颤栗,说不害怕是假的。此时,若唐知谦在家,多少能有些底气。
“大娘子,外面在叫喊的,是……是一个穿戴整齐的老爷。”
“老爷?谁家的老爷,这时候来添什么乱!”思虑片刻,我赶紧追加道:“赶紧将他悄悄放进来,千万别叫那几个契丹人看见了动静。”
若是平日里,大可以由着他站在府外,由下人询问好再决定要不要请进来。可如今,事出突然,只能将他慌忙请进了府里。
“温老爷!”
我一看,这个老爷不是旁人,正是此前胡搅蛮缠的温如歌的父亲。
“哟,大娘子好眼力,我以为你是不大认得我的。”
温才峰大抵是以为自己才气过人,此等威名竟然已经传到了汴京。因此,见我一眼就认出了他,已经顾不上行礼,脸上堆满了笑容,挤得右脸的大黑痦子跟着身体一起跳舞。
我也跟着笑,嘴上跟着迎合道:“自然是认得的。”心里却忍不住嬉笑怒骂,我哪里是认识你温才峰,我分明是还记得你脸上长着长毛的黑痦子。
“温老爷,什么风把您吹来了,眼下我实在无心招待,若有要紧的事不如长话短说。”
这话是真的,眼下,一屋子老老小小需要我挂心,大街上还有三匹恶狼一样的野蛮人,哪里顾得上听他唱戏。再者,前脚送走了小的,后脚又来了老的,是福是祸尚且说不明白。
温老爷显然不在乎我的话,自顾自找了椅子坐下来,变了脸色,侧着身子对着我怒目圆睁,谴责道:“我说大娘子,您如今好歹是这侯门中管事的,怎的能如此草芥人命?”
“温老爷这话打哪里说起,我一个妇人,终日在这院子里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,怎么就和人命官司攀扯上了。”我虽然对这个温秀才早已耳闻,可有些人,当真是百闻不如一见,温如歌蛮不讲理的个性,果真是随了他。
温老爷将脸一沉,从腰间拿出了一方用帕子包裹着的破碎镯子,伸出了半臂,用右手指着躺在左手的零星物件,怪罪道:“您瞧,这镯子,大娘子可认识?”
“我不认得什么镯子,温老爷该回家问问自家姑娘,认不认得。”
我的心里一团迷雾,尚且不明白这个温秀才的肚子里在谋划什么,只能装聋作哑,等他自己耐不住性子,自然会跳出来一五一十说个明白。
“大娘子不认得?”见我没给什么好脸色,温秀才干脆站起身,托着一手破碎的镯子又向我走进了几步。凤兰赶紧上前来阻拦,这才将他重新劝退到了本来的位置。
温秀才继续义正严辞道:“这可是你们汴京侯府的东西!哼!”
我仍旧不说话,警惕地将茶杯靠近鼻尖,拂手嗅了嗅香气,问道:“哦?何以见得这就是我们侯府的东西,难不成是上面印了字?”
“大娘子也休要装聋作哑,这镯子乃是那日你吩咐人送我女儿回家时,构陷她偷东西的证据!”说到这里,温秀才愤恨地将破碎的桌子往椅子上一扔,自己则背对着站立,两只手饶有趣味地放在身后继续盘算。
听到这里,我总算有些明白这是在唱什么戏了。于是,我客客气气地让凤兰把那用帕子包裹着的镯子拿了过来,翡翠镯身,透亮温润,显而易见的品质极佳。
“温老爷说这是……构陷?可有什么证据?”我慢悠悠说道。
温才峰适才转过半个身子,斜着脑袋,逆着光看去,不大能看得见他的眯缝眼,只能瞧见脸上的黑痦子嚣张跋扈,他从鼻孔里挤出来一腔不屑,说道:“这还不算是证据?这镯子正是侯府中的物件,本不该出现在我们温家。只因我家小女上次来府中拜谒,与大娘子生出了些许不快……”
说到这里,温秀才忽然停住了,不再继续往下说,可,即便他不再说下去,在场众人也听得出来这是何意。说破天了,不过是想指责我心眼子小,为报复温如歌,这才暗中构陷污蔑。
这父女二人,当真是蛇鼠一窝!
“温老爷,东西可以乱吃,话可不能乱说的。”如此提醒了一句,他便果真心虚不再说话,兀自又将身子背对着我。
“温老爷,这镯子究竟是我派人带进温家,以此构陷你家女儿的,还是你家大娘子留给女儿的遗物,只凭我们两张嘴,恐怕难以说得清楚。”
温才峰将身子完全转了过来,气定神闲地往椅子上一仰,得意地接过话茬:“大娘子说得正是。这事情,说大不大,说小不小,若传扬出去,却实在有辱大娘子的声誉,这实在不是我愿意看到的。”
见我不说话,他忽地站起身来,在宽敞的屋子里来回踱步,低着头佯装替我想办法,嘀嘀咕咕一阵子,恍然大悟道:“有了!不如这样,大娘子同意让我家如歌入府做妾,对外便只说这镯子乃是侯府的人千里送礼。想来也不会再有人去追究了。”
“温老爷当真是好法子,劳烦您替我挂心。”我面上虽然客气,心里早已咬牙切齿。此刻想息事宁人,免不了要费一番心思了。
温才峰眼珠子滴溜溜一转,随即喜笑颜开,说道:“这么说,大娘子答应了?”
“本就是一桩小事。说起来,倒是温老爷气量过人,自己手里的掌上明珠,温家实实在在的嫡女,竟然舍得放在我侯府为妾。”打眼瞥过去,温才峰的脸上甚是尴尬,只好敷衍着笑了笑。
“女大不中留,虽说妾的名声不好听,可,到底是镇国公侯唐家的妾,比之外头百姓的正妻,不知道强多少。”说着说着,他竟不自觉乐出了声音,好像捡到了一桩不得了的买卖。
“温老爷倒是替女儿考虑得周到。”
“那是那是,自家姑娘,岂有不为她筹划之理。这,这心思,天底下的父亲都一样。如若不然,江老爷也不会费尽心思让您来侯府做了正头大娘子……”
最后的一句话,虽然声音极小,可到底是分量十足,顺着一股子邪魅之风悠悠传进了我的耳朵。我自然晓得,父亲当年冒着让我守寡的风险嫁进唐家,也不过是想借牺牲女儿的幸福为他荡平康庄前程。
可,人与人相处讲究一门子学问,他既是有求,便不该戳我痛处,如今的吃相不免龌龊了些!
我略略整理好脸上的神情,应承着他的话,问道:“那,温大姑娘现在何处,可跟着温老爷一起来了?”
“来了来了,就住在东街的如家客栈!嘿嘿,大娘子既然已经允了这事儿,我即刻就出门把她带过来!”这么一边说着,温才峰便要跳着蹦着出门去接人。
“慢着!”
想到街上此刻并不太平,恐惹来祸事,便赶紧阻止了他去开门。一边笑着测试道:“我既已经同意您的请求,便也不急于这一时见到人。晚些时候,等签了协议,我再亲自找人给她抬进来。”
“协议?大娘子说得是何种协议,我怎的没听说过这门规矩?”温才峰疑惑道。
“外头的鲁莽人家,自然和侯门官宦人家不同,温老爷也是看中了这一点,是不是?”说完,故意别有用心地瞧了瞧他。
温才峰大概也猜出了我的指桑骂槐,手足无措地跟着应承说“是是是”,又饶有戒备地抬头问了一句:“不知是什么样儿的协议?”
“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,不过是让温大姑娘答应……”我故意停顿了一会,仔细瞧着温才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便提高了嗓门道:“叫她答应和温家断了来往!”
“大娘子,这,这这,这是哪门子规矩?哪有要了姑娘,又不要娘家的说法。”
“温老爷,您自己说的,让姑娘进侯府为妾,乃是为了她将来的前程。如今,我允了您这门心思,按理说,您便该是心满意足。”
温才峰将脸子往下一拉,吼道:“大娘子,我算是理清楚了,您打一开始就不想答应这门亲事。如此,倒也别怪我将侯府做的欺人恶事闹得人尽皆知。”
所谓欺人恶事,无非是之前那件关于“镯子”的事情,再三提及,当真是以为抓住了我的把柄。
我忍不住呵呵一笑,姑且也从椅子上站起来,面向温才峰走了几步,不紧不慢说道:“适才你说得那个镯子,实则是你家大姑娘在我府上住了一夜后,声称是要紧的亡母遗物,我这才好心派人跟着从汴京找到了扬州。可我现下瞧着,你家大姑娘许是不会承认这一点了。”
温才峰不说话,眼神慌乱地看了我一眼,又赶紧将目光望向了别处。
“不管温老爷信不信,我确实不认得什么镯子。”
没等我继续往后说,温才峰竟擅自打断了我的话,紧跟着说道:“这一切,也不过是大娘子的一面之词……”
“温老爷,我家大娘子确实不认得什么镯子,可你们扬州西葫芦巷子里、吴氏当铺的老板却记得明白。听闻您从前曾拿着镯子要找他换钱,岂料那镯子虽然值钱,却达不到您心里的数目,这才没做成这笔买卖。”凤兰挺身而出,三言两语倒是说了个明白。
自打见识了温如歌的品性,为保完全,我自然要派人暗中将整个温家上下查个明白,便是温才峰第二房妾室生的儿子并非温家亲生骨血的真相,也跟着浮出了水面。
想来温才峰是不知道这顶绿帽子的,如此才对家中唯一的儿子心疼至极,即便是推大姑娘出去做妾,也千方百计要为这个小儿子保全仅存的家业。
温才峰见自己并不占理,又害怕我果真找了吴氏当铺的老板来对质,只好装作哑巴站在原地一声不吭。
温才峰变换了脸色,谄媚一笑,抬起手又向我拱了拱,说道:“我这个老头糊涂,同大娘子开了一个不适宜的玩笑,还望大娘子不要计较。”
见我不理睬,他想了想,还是决定鼓足勇气老话重提,说道:“我们温家本就是个普通百姓,我如今上了年纪,家里头小的小,弱的弱,实在没什么指望。可我瞧着,侯府的田地产业何止千亩,铺子店面不下几十家,银两钱财更是数不胜数……”
“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?温老爷一大把年纪了,却倒有脸惦记别人的家业!”凤兰干脆利落地怼了一句,温才峰虽然不大高兴,可到底懂得一些场面功夫。
温才峰迎合道:“对对对,如今我一大把年纪,实在是没有颜面说这些话的,可,可我这也是没有法子。大娘子,你瞧着这么办行不行,协议我签,但今日你得多多少少给我一些好处……”
此处声音小了一些,忽然又听他吊着嗓子,慷慨激昂道:“这花朵一样的姑娘,好歹是我生的、养的,也不能白白送给你们啊。”
为给庶出的弟弟谋份家业,狠心父亲将她这个嫡女,卖去做妾
你瞧,这世上多的是自私虚伪的人,一面说着自己全心全意牵挂女儿的前程,一面始终牢记自己的钱财利益。说到底,如歌姑娘是不值得怜悯的,她岂能不知自己的父亲如此薄恩寡情。
“温老爷,您说的话,我越来越听不明白了,一会子在这唱构陷的戏码,一会子又跟我聊大姑娘的前程,这会子,怎么倒像是跟我攀扯卖闺女的价钱了?你若是舍不得,我正好也懒得处理这门子喜事。索性算了吧。”
我一边说,一边转身慢悠悠向着不远处的门口望去,仔细听外头的动静,想着赶紧打发这无赖的老油条。
“我……大娘子,你就看在我家姑娘与您家有缘的份儿上,姑且依了我吧。您放心,待如歌入府,我定嘱咐她好好服侍您,当牛做马,悉听尊便。”温才峰信誓旦旦地将此话说完,便用一种坚定期盼的眼神注视着我。
我忽然又觉得如歌很可怜,同我一样可怜,我们不过都是牺牲品。
心里的防线后退了几分,倘若温如歌从今往后能一心向好,我倒也不是不能容她。
我朝着凤兰暗中使了一个眼色,她立下心领神会地趴在墙根去听外头的动静。
凤兰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,回来禀报说,外头现下安静得很,爬上墙头往外头看,也不见街上有什么恶人了,三三两两的商户也在小心翼翼张着脑袋往外查看。
2
如此,凤兰携着三两个小厮女使,跟着温才峰去了东街的客栈。
只是,回来时,并不见温才峰父女,凤兰的后头倒是跟了一个极为熟悉的男子身影,用宽大的蓑帽掩着面,着一身棕褐色的素衣常服,离得远,只能依稀瞧着是一个健壮的年轻人,却实在看不清模样。
待领了人从院子里走到内室,方才看出此人的真面目。
“江……江甫尘!”
我惊恐地叫出了声音,随即又赶紧捂住了嘴巴。他这才放心地把帽子拿了下来,扬起嘴角朝我笑了笑。
上一次见他,恍如隔日,如今再见面,中间横竖隔了不过一年多,他明明还是那般温润如玉的样子,可瞧着竟始终不如从前俊朗明媚。
若不是这脸上挂着的几分笑意,让我觉察出来,这就是曾经在江府竹园同我嬉笑怒骂的少年,我或许已想不起他快乐时候的脸色。
“你怎么来了!”虽是带着满心欣喜问出了这话,可心里难免惆怅万分。
当初,他在官家面前允诺,无诏不得入京,如今算是违背了诺言私自回京,这若是叫有心之人瞧见了,免不了又要做一些文章。
好在当下是年关,各家各户都在奔忙,无暇顾及旁人。自打唐知谦被支出了汴京,唐家的眼目也少了大数。
不等江甫尘说话,凤兰便严肃着一张脸,支支吾吾道:“大娘子,我们跟着温老爷进了客栈,可……可瞧见的……”
“嗯?温如歌不见了?”
“这倒不是,温家大姑娘是在的,躺在床上……”凤兰又只说了半截子话,便不再敢继续说下去。
凭着我能对凤兰的了解,若不是出了什么诡异的事情,她绝不会是如今这副惨白如纸的脸色,便是方才领着江甫尘进门,也不见得她有什么喜悦的容颜。
“可是出了什么事情?怎么不见温家父女二人与你一起回来?有什么话就说,天又没有塌下来,你怕什么呢!”
凤兰微微侧着脸看了一眼江甫尘,咽了一口唾沫,低着头说道:“我们赶到的时候,敲门不见里头的人答应,温老爷便领着我们推门而入。可,眼前看到的……只是温大姑娘四仰八叉躺在床上,脸上、肩膀上,都……都是鲜血,衣服也早就被撕扯烂了。很是怕人。”
“怎么回事?当真出了盗贼?”我浑身发凉,竟没想到在汴京中还会出这样胆大妄为的事情。
“奴婢……”
见我主仆二人为了这桩事讨论不休,一旁的江甫尘总算不再沉默,抬起手打着手势想要说明什么,却始终让我看不明白。
“你……你不能张口说话了……”我随即反应过来,没来及细问原因,眼泪已经控制不住地跟着落下来。
他的身上留着官家的骨血,本是高高在上的六皇子,被褫夺亲王封号,遣送三千里之外,无诏不得入京。这本就是一桩洗不清的冤情,如今……
“说起来,还是五哥儿救了温大姑娘呢。根本没有什么盗贼,实际上就是那三个契丹人闯进了客栈,碰见了温姑娘下楼,起了色心,这才……这才追着温姑娘到了房中,夺门而入,侮辱了她……”凤兰帮着说话,嘴里仍旧称呼他为五哥儿,江甫尘则站在一边点头附和。
我压制住颤抖的声音,扶着把手坐在榻上,一字一顿问道:“那,那温大姑娘现下如何?”
仍旧是凤兰说话:“我们赶到的时候,那几个契丹人正要翻窗户往下跳,可楼下走着的正是五哥儿,没几下就把那几个人就地正法了。”
说罢,她又看了看我,紧跟着回答说:“至于温大姑娘,人倒是还有一口气,两只眼睛木木瞪着,不说话,也不动弹。”
我虽并不喜和温如歌打交道,料想她也不过是受了温才峰的言语蛊惑,加上亲生母亲和外祖母的宠爱,恃宠而骄,这才瞧着让人生厌。可我却也属实没想到,她会有如此遭遇。
我遣人拿了一些银两带给温才峰,带了两三句安慰的话,嘱咐他好生安顿自家姑娘。
回来的人禀报,温才峰并没有接受钱财,乃是将银子掀翻在地,对着派去的女使说,这是下贱的施舍,又扬言定会来上门讨公道。
次日,温才峰果然不请自来,身后用绳子牵着一位蓬头垢面的姑娘,正是那日惨遭不幸的温如歌。
那温如歌已然失去了人性,一会哭一会笑,一会跳一会叫,总之很难再如从前大家闺秀般安静站着。
温才峰找了一根指头般粗大的绳子,一头系着女儿的腰,一头攥在自己手心里,怕她走丢,又怕她不走,于是,便走两步,用力扯一扯手腕,拽得后头的温如歌一惊一乍,嘻嘻笑笑跟着往前走。
温才峰来的时候,江甫尘在后院,以他的身份,自然是越少人知道他的踪迹便越是安全。
“温老爷。”
这么客气地叫了一声,我就实在不该说些什么话了,看他通红的、愤恨的眼神,自是来者不善。
走到了院子里,他还径直要往我面前走,却被凤兰派人拦住了。
温才峰冷笑了两声,将绑着绳子的手腕慢慢抬起来,转身指着身后疯疯癫癫的温如歌,说道:“大娘子,我送女儿来侯府做妾啦!”说完,又情不自禁发出阴森恐怖的笑声。
我实在怜悯他,便自然多了三分客气,用宽慰的语气缓和说道:“温老爷,我知道您的心情,发生这样的事情,实在是令人痛心。可如今,你也瞧见了,温大姑娘这副样子,我还怎么能留她在身边呢,不如你带回扬州好好照顾,兴许还有康复的指望啊。”
“我呸!江晴鸢!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歹毒的妇人,为了不让我女儿踏入侯府分享宠爱,竟声东击西找人糟践了她!我不管,如今只要她还活着,那便就是你们侯府的人。”温才峰不容分说地解下了自己手腕上的绳子,将绳子重重地朝地上一丢,别过脸看都不看身后还在喊着“爹爹”的女儿。
“温老爷,早前我告诉过你的,话不能乱说,你这是看侯爷不在家,我一个妇人好欺负吗,居然几次三番往我身上泼脏水。”讲到这里,清了清嗓子,又继续抬声道:“这里是汴京,你是以为衙门没人能管你了吗?”
本是顾念他爱女心切,实在不成想,到如今这步田地,他仍旧不忘痴心妄想,跟这样蛮横不讲理的人打交道,又还有什么情面可言呢。
温才峰适才变换了脸色,不似方才那样倨傲,却也不如昨儿奉承,冷着脸问道:“那依你所言,如今就打发我回扬州?大娘子,你未免想得容易了些!”
“你真是个泼皮无赖,当真以为我们侯府没人能治你了吗?”凤兰插话道,我当下浑身汗毛竖立,赶紧勒令她住嘴,唯恐这丫头一时气盛,把不住自己的嘴,眼瞧着就要把六皇子在府中的事儿说出来了。
“胡说什么!温老爷到底是个斯文的读书人,你身为侯府的女使管家,怎的这般没规矩。怎么,难不成是我从前高看你了?”说完,故意做出恼怒的样子,斥责凤兰退到后院等候发落。
这丫头跟着我的日子久了,自然能猜得到我哪句话是真,哪句话又是场面话,兀自领了责罚退了下去。
温才峰听得出话音,知道我乃是借着骂下人的名义,其实是在给他脸色,“斯文”、“高看”都不过是在指桑骂槐。料想一个读书人是听得懂这番反话的,否则也不会就此收敛了德性。
“大娘子,我原本不是爱财之人,早年间也有科考走仕途的打算,可……哎,如今拿这些陈年旧事出来卖惨,实在是羞煞人。”温才峰总算说了两三句“斯文”的话,摇摇头低垂着脑袋,少了许多嚣张和蛮横。又抬起手伸到自己的眼角处,蜻蜓点水似的抹了抹。
不过是一瞬,他又生出了几分主意,笑着说道:“大娘子,你是好人,现下,我温家落魄了,又摊上了这桩倒霉事,免不了回扬州要受尽白眼,如此还想谋一份差事,实在是难上加难。”
“温老爷,我自是知道你的难处的,我也还记得姨妈的话,说起来算是沾亲带故的。”
“对对对,您算是说着了,我们两家可是亲戚!”温才峰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,将最后的两个字说得又慢又重,抬起手在空中兴奋地划了一个手势。
我抿着嘴敷衍着微笑,很客气地搪塞道:“却也算不上亲戚,若不是您托人带着温大姑娘来府上,我还真不曾听侯爷提过呢。想着以后来往也不会多了,您说呢?”
温才峰并没有否认此前拜托钱姨妈的说法,思忖再三,还想张口说些什么。
即便他不说,我也是要说个明白的。
“温老爷,说句实在的,若不是看你家温大姑娘可怜,现在也轮不着你站在这里跟我又骂又哭的。”
“是是是,多亏大娘子心肠好。”
“多余的话不必说了,我给你二百五十两银子,你且拿着这些钱去做些营生买卖,养活一家子吃穿,不成问题,若你能吃得下苦,东山再起也是有的。”
“大娘子恩德隆重,上达于天!只是,做生意,从投入到回本赚钱,中间少则几个月,多则几年也保不准,那……那这段时间,一家老小,岂不是要喝西北风?”
“你的打算倒是精明,那依你看……”
温才峰抢过我的话,迫不及待地出谋划策道:“恳请大娘子赏赐几亩田地,缓解我燃眉之急。”
说完,赶紧跪倒在地,将两只手拱着,慢慢高于头顶,嘴里念念有词,又补充了一些旁的逢迎之词。
“从二百五十两银钱中,抽出一部分买田地,置产业,不是不行。我瞧着啊,温老爷未免过于精明,倒不如孑然一身,任我打发来得爽快!”说完,我随即一声令下,喊来了四五个身强力壮的小厮。
“说笑,说笑。方才都是糊涂话,就依照大娘子的办法。”
说完,爬起身,等着领银钱。嘴里念念有词:“越是有点钱的人家,越是小家子气!”
“不着急,温老爷,你来把这份契约签了,我马上就派人给你拿钱,一并找轿子送你们回扬州。温大姑娘藏在轿子里,也绝不会叫人瞧见惹来笑话。”
“还要签契约?”
“自然是要的,天上从不会白掉馅饼,是不是?”
温才峰谨慎地接过我手里拟好的契约,上下打量了一遍,不可思议地问道:“你这是……这是要断绝来往,还……还要我答应从今以后不再踏入汴京?你也不过是一个庶女,何来这样大的口气!”
我走过去,笑着将他手里的一张纸又重新拿了回来,慢慢拿在手心里对折,一边说道:“呵,可不嘛,是庶女,才敢这么做呢。”
心下想着,既然和你们温家扯上关系,这本就是没有脸面的事情,比起什么嫡女庶女的名声,我更不愿往后的日子再三受到威胁叨扰。
“不愿意也有不愿意的法子,那就请温老爷怎么来的,怎么出去吧。如若不然,我可就叫人像打发叫花子似的赶出去了,那才是真的不好看呢。”说完,便朝着站在两侧的小厮使了一个眼色。
温才峰本就是个欺软怕硬的,见状感激委曲求全,说道:“拿来拿来,签就签。哼!有钱总比没钱好。”
说完,一把抢过我手里的纸,叫人拿来了笔,张开嘴放在舌头上润湿了,干脆利落地签上了名字。
如此一番折腾,总算送走了温才峰这座难缠的瘟神。
3
趁着府中终于安宁了,我也才终于能腾出空来和江甫尘好好聚聚。
如今,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,只能通过写字的办法与我交流。我不愿意在他面前流露出悲楚的样子,只得半开玩笑地说:“你的字进步了不少。”
趁着身边没有旁人,我索性直接问话:“你……你的嗓子……是生了病?”
江甫尘想了一会,伸出手重新拿了一张干净的纸,皱了皱眉,又舒展开额头,低头写下了两个字:“中毒”。
“中毒!”我惊叫出了声音,又压低了嗓音问道:“谁下的毒?”
他笑了笑,似乎没有告诉我的打算,本来拿在手心里的笔,竟然在这时被他决定放下来。
他忽然变了脸色,黯淡悲凉,从一双深邃的眼眸里,再也望不到明媚的光芒。
我却终于松了一口气,打从见他第一眼开始,江甫尘就一直抿着嘴巴冲我笑,只有我扭过头,用余光扫到他,才能偶然看到他脸上失落的真实面目。我晓得的,他不过是在想尽办法让我宽心。
可,他到底比我要辛苦许多,事到如今,竟然还想着为我减少忧思。
如今,终于看到他卸下伪装,我才终于觉得我们中间更加熟络,多少有了一点从前朝夕相处的影子。
见我仍旧不罢休,再三追问下,江甫尘这才悻悻地在纸上又写了两个字:“皇上。”
这个答案,我不是没有想过,舐犊情深,相比之下,我倒更加宁愿用尽无耻手段的人是其他皇子。
毒哑,便能藏得住诸多恩恩怨怨了吗?
我故作冷静,不敢大声说话,又实在气得浑身发抖。江甫尘站起身,走到我身后,抬起手轻轻拍拍我的肩膀,示意我不必难过,多余的话倒也没有再写。
“那,那苏绣如何?”
既是夫妇,江甫尘被下毒的时候,此人又在何处。
江甫尘的手停在了半空中,迟迟没有再落下,重新坐在原来的位置上,眼神仍旧悲伤难掩,写道:“死了。”
分开不过数载,这汴京还是一如既往风平浪静,可是在离汴京三千里以外,风云变幻已然辗转万千,从前允诺的岁月静好,到底还是成了一句笑话。
江甫尘见我震惊失色,又在纸上补充道:“难产,一尸两命。”
瞧着不过是几个字,很快就写好了。可这几个字背后,又该是何等的心酸。
女子生产自然是走一趟鬼门关,可谁又能说这件事只是意外。那苏绣是个练家子,身体康健不说,便是江老爷爱女心切的心性,也定然时时刻刻派人照料。
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圣心,倘若诞下的是个男婴,不亚于是为复辟势力添了一枚得意的棋子。这些终究只是不能说出口的猜心,我能想到的,江甫尘又怎么会从没有过半点怀疑。
官家并非是忌惮这一生一世一双人,乃是怕子嗣绵延乱了朝纲。
我还记得,前些年,我初次去苏家为唐知谦提亲,那是第一次见到苏绣,不比其他女子温婉柔弱,浑身散发着大义凛然的朝气,更藏着几分拔刀相助的豪气。
彼时,我嫉妒了她好一阵子,或许是来自江家老爷对女儿的偏爱,我从未享有;又或许是得知江甫尘亲自恳求官家赐婚,我惘然若失。可我终究还是祝福她的,那样有灵气的姑娘,生来就注定要享受世间万千偏爱。
我不知中间是出了哪些岔子,竟导致一尸两命的悲剧发生,我也再不敢向江甫尘细问详情,以免唤起他本就惨淡悲凉的回想。
我哽咽着,从他颤抖着的手中,拿出细长的毛笔放在砚台上,到底是没忍住,两滴眼泪跟着落在了砚台的墨汁中。
“那,如今,你又是一个人了……”
我很不想这么说,这样伤感的心思本该在脑子里一闪而过就好,如今情绪难掩说了出来,与其说会增加江甫尘的感怀,倒不如说,惹得我更加心痛怜悯。
江甫尘低着头偷偷叹了一口气,慌忙收拾好通红的眼眶,咧着嘴巴,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,冲着我做了一个鬼脸。我又难过又好笑,最后便只能忍不住跟着笑。
官家极为看重权力和自己的颜面,无诏回京乃是大罪。江甫尘看出了我心里的担忧,恢复之前言简意赅的样子,只在纸上淡淡写下两个字:“路过。”
“我还以为你是记挂我,特地偷偷回来看望我的呢,哎,到底是自作多情了。”我开着玩笑,噗嗤一声笑出了声音,江甫尘这会子又跟着我乐。
我自然还想继续打破砂锅问到底,比如,路过汴京,那目的地是哪里?以后有何打算?
话明明都已经到了嗓子眼,想了一会,还是垂下了脑袋,又将那几句饱含个人疑惑的话憋了回去。天涯海角总会有容身之地,只要一点,别留在汴京。
汴京辉煌热闹,唯独与他无关。
江甫尘见我沉默不语,不动声色地在纸上继续写道:“我们终会再见。”
心里涌出一股暖流,但愿再见时,你已经是自由身,倘若想得再奢侈一些,希望你比现在欢乐。
夜色之下,街市上也总算不比白天热闹,趁着城门还有半个时辰就要关上,江甫尘换了一身玄色常服,藏在轿子里,由我护着安全出了汴京城。
等到了郊外,天色已经如墨染,深冬的野外除了能听见刺骨的寒风在树林里乱窜,再也寻不见更多的风景。
这会子,清早派人收拾好的马匹和行李也来了,江甫尘肃立在马前,从满面愁容的脸上挤出笑意。好像这就是最郑重的道别了。
回去时,府中依旧灯火通明,女使们都笑嘻嘻地忙碌。
原来,明日就是除夕了……(原标题:《庶嫁:构陷》)
点击屏幕右上【关注】按钮,第一时间看更多精彩故事。
(此处已添加小程序,请到徐博客客户端查看)